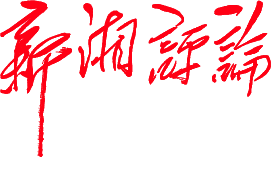细柳滩
这片河滩是没有名字的,说来也是它太过普通,无非就是老家望城乡下沩水河边一块太平常不过的小河滩而已,但对于我和堂叔来说,却是记忆里弥足珍贵的所在,是童年不能忽略的寄生地。
十岁那年回到故乡,暑假时候正值“双抢”,没有闲人来照顾,但出于小时候亲近的情分和喜爱,隔壁家的叔奶奶要我从她四个儿子中选一个出来陪伴,这是亲戚间的客气,也是没有女儿的她对我的偏爱,当然我不出意料地选中了她最小的儿子,只大我两岁的堂叔。十二岁正是半大小子,也可以做半个劳力使用,可堂叔偏偏瘦小不扛力,在田间打个下手还常被嫌弃动作不够麻利,所以用来照看我倒是正合适。
说是照看,其实也就是带着玩儿。他的玩儿更多的还是打理家里的事情,对于我来说则都是新鲜的游戏。清晨早早唤起床来,顶着露水去推鱼,用旧蚊帐做成的推子顺着长长的竹竿伸到水塘深处,停留片刻再拖上来,那蚊帐布里就困住了许多的小鱼虾,细心地捡出来丢进水桶,再把碎石、螺蛳、蚌壳甚至是粗壮光滑的牛蚂蟥翻倒掉,又可以再推。第一次我看着那缩成一堆拳头大小软软黏黏的牛蚂蟥尖叫,却见他毫不在乎地用手拈起一甩好远,瞬间觉得这个从小只被我叫唤着外号的堂叔高大了许多,顿时心生一种膜拜。过后没几天,我也能捏着这玩意儿扔出鱼推子了,据说蚂蟥繁殖能力特别强,只有用火烧才能让它无法复生,但一直没有机会验证。
推完鱼虾便是下河渠捞水草,等到背着一大篓水草、提着鱼桶回家,跟着还要去菜园浇菜。夏天日头大,菜不但要每天浇,而且要赶在日头出来之前浇,这样才不会把菜根灼坏。堂叔教我清水可以从菜畦上大幅度动作地抛洒,而粪水就必须用长柄勺细细地挨着菜根浇,每颗都不能浇多了,因为粪水营养而珍贵。从他那里我懂得,拉屎拉尿最好都回自己家,以便攒肥,这些城里人羞于提及的话语从他嘴里说出来自然不过,从粪池里舀粪和加水稀释的时候也很是认真,只有在这时候,我才不会像城里孩子通常的那样矫情地捏住鼻子扭捏,而是通过这些举动仰视他对农事的郑重。
忙完了这些才赶上早饭,过后日头渐辣,他还得带着我洗洗涮涮收拾家里,剁了早上捞的水草和米糠熬成潲水喂猪,鸡食也打理好,这才牵出牛羊来赶往河滩。
去河滩才算真正的玩。在沩水河上,这是一处寻常不过的小河滩,像个芒果的形状,只有芒果尖头的部分,不到两米的宽度和河岸相接,其他近八成滩岸都在水里泡着,远远看上去就像一个小岛漂浮在河里。这样的河滩太多了,从长沙城里上沩水桥一路过来,大约七八公里都能看见近十个,并不稀奇,只是它面积略微大些,不像那些河滩只长青草或孤单三两棵树,而是栽满了柳树,满滩的柳条儿像女孩的长发随风飘荡,河滩就平添了些许妩媚柔美的气韵,显出和别处不一样的风情来。
夏季正是丰水期,充足的水量侵蚀了堤岸,许多地势低的柳树都泡在水里,我们在草丛里抓蚱蜢、捉知了、在树干上跳来跳去攀越水中的柳树。
可以玩儿的东西多了,多数一学就会,但唯一没能学会的就是钓鱼。坐在树墩上,柳树粗壮的树干正好挡住炙热的阳光,水面上吹来的风湿润清凉,头顶成片的树阴,柳条儿飘来荡去撩拨着脑袋,有时候还要不甘寂寞地骚扰到水面,挑逗似地点点戳戳一阵子,泛起涟漪变成大小圆圈扩散开,就如同闲得发慌憋不住去捣蛋的小孩……如果没有连番的蝉声聒噪,这实在是幽静至极,适合遐想。堂叔举着钓竿一动不动地盯着浮漂,可我常常是心猿意马左顾右盼,不是琢磨牛和羊,就是被忽然而至的蝴蝶牵走了眼神,哪怕什么都没有,一切都是静止不动,也能看着远处近处垂下的柳条愣神,怎地就能生得如此婀娜纤美——总之,心思完全不在钓鱼上面。
堂叔是钓鱼的高手,他有很多自制的鱼竿,分别用来钓油鱼、草鱼、财鱼等等,这天他带的就是专钓无鳞鱼的油鱼竿子,因为我喜欢吃肉嫩刺少的黄姑鱼,他允诺钓三四条让我尝鲜。这种鱼深黄背淡黄肚皮,浑身光溜溜,嘴巴瘪瘪,嘴角两条须,背上和两侧分别长有硬硬的长刺,据说会发出像鸭子一样干瘪的叫声,所以乡下也叫黄鸭叫。看着就快到要回家做午饭的时间了,可鱼篓里还只有个头不大的三条黄姑鱼,显然是做不出一碗菜的,他有些着急,却也知道急不来,只是铆足了劲跟鱼竿死磕,盯着浮漂皱着眉头好像整条河都欠了他似的。
其时我已经坐得有些不耐烦了,无声地将裙子撩过来撩过去,只希望他看出我已经坐立不安早些收场,但他根本不看我,眼光觑着水面,嘴微微地撅着,忽地眼睛一亮,就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瞬间,已然起身,鱼竿也顺势一抬,一条壮硕的黄姑鱼被鱼线拽出水面,正使出浑身的力气拼死扑腾,他喜出望外地收线,熟练地将鱼线一荡,作势就要用手抓住,意外出现了,鱼线由于黄姑鱼的重量和挣扎之力偏移了原本的弧线,眼睁睁那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我飞过来,鱼背上的刺猛地扎进了我的膝盖!
野生的黄姑鱼重达八两多很少见,他大概也没有想到会如此意外地创下自己油鱼钓史里最好的战绩,只是自制的油鱼钓竿只考虑了通常无鳞鱼的个头,并不匹配这条大鱼,才会失控让我的膝盖被扎。当我一瘸一拐地回家,硕大的黄姑鱼也没有成为立功品拯救堂叔,他还是因为对我照看不周被他妈痛揍了一顿。从那之后许多年,我都不曾再吃黄姑鱼,因为每当看见黄姑鱼,我就会想起这个小堂叔被痛打时不躲不闪、满脸泪花的委屈模样,当时的心疼总是伴随着深深的自责,令我对黄姑鱼再也没有任何的食欲。
这大概就是我对这片河滩最深的记忆,它承载过我童年所有的欢乐,也第一次教会了我什么是感同身受,什么是心疼。
时光缓慢地流逝,等到我再回故乡又是六年之后。兴冲冲地放下行李,奔到隔壁去找堂叔,却见他收拾铺盖准备出门,说要和哥哥们一样去城里打工。看着堂叔离家出门的背影,我再一次心疼。
过后好些年,不知道辗转了多少个城市,他终于回到长沙。有一年快到春节了,他上门来借钱,说是筹集了些钱垫资做基建包工头,带着乡里乡亲出来做事,没想到施工方拖欠工资,他要不到工钱,而乡亲们都聚集在他家,等着他发钱回家过年。我竭尽所能地凑了些钱,送他出门,看着路灯下他孑然的身影,泪水不觉滑落。
等到来还钱的时候,他的神色已经轻松不少,坚持要给利息,说国家有政策规定不准欠薪,现在基建工钱都有人社部门担保了,他挣了钱便不能亏待我。我坚持不要,最后他让步,放下一个油漆桶走了。打开桶盖,看见满满一桶大小不一欢脱游动的黄姑鱼,我湿润了眼眶。
又过了几年,他渐渐发达,工程越做越大,还开了个车行,承接各种旅游包车,有空的时候也常常接我出去吃饭。
忽然有一天,他打电话来,说结束了所有生意,回老家了。我惊诧莫名,追问原因,他只是嘿嘿地笑着,故弄玄虚地说明年开春就能知道了。一年之后我被他拉回了老家这片河滩——他跟乡上商定了土地流转,承包200亩的土地经营权,开办农庄,让散居的农户集中到新楼房里居住,其他土地用来种植经济农作物并进行农业旅游开发,而且在河滩边上新建了民宿楼房。就在我去的当天,早有捷足先登的一群艺校学生跟民宿签下了长期包租合同,三三两两去往河滩上写生。
“现在,农村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,而且,我们能和城里人一样生活得很幸福……”他回头看看我,眼神晶亮,一如少年时候。他指指河滩边上新立的一块大石头对我说:“我按你说的,给这片河滩起了个名,下一步就要做旅游推广,让城里人都来玩!”
我说的?他将一脸狐疑的我拽近,眼见硕大的三个绿漆字“细柳滩”。
记忆忽如潮水般涌来。在那个夏日的早上,穿着碎花裙的女孩跟在瘦精精的小堂叔身后,穿过密集的柳林,望着在无数绿丝绦摆动间隙里清幽流动的一江碧水,不由得冲口而出:“多么漂亮的细柳滩……”
- 新湘导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