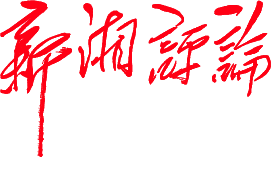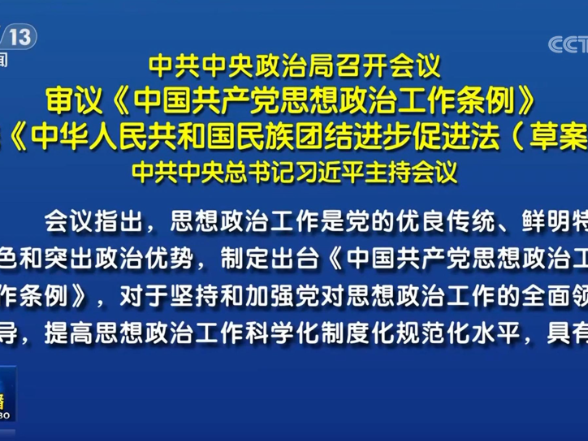淦田记

看多了古镇古街,我对株洲淦田老街起初并没在意。我在老街上心不在焉地逛着,也胡乱想着:淦田老街算破不算老,新旧掺杂,连个雕花木窗都没有,也没修旧如旧,是为了保持自然原貌,真实呈现?
一户人家后窗下的花让我驻足。花是渐变的金色,呈喇叭状,别致妖娆。
同行者说,这是曼陀罗的一种。
提到曼陀罗,我霎时想起香港作家亦舒,想起读《曼陀罗》的少年时光。
大伙儿围拢拍花,奉姐用手机扫一扫,遗憾道:“这是洋金花,不是曼陀罗。”先前说曼陀罗的文友笑了:“洋金花就是曼陀罗的一种呀!莫去摸花,它周身是毒,嗅久了也容易致幻,华佗的麻沸散、古人的蒙汗药都是从曼陀罗中提取的。”她介绍的时候,我正凑近一朵曼陀罗反复拍,听说会致幻,猛地收回了手。
经过那丛曼陀罗,方知折出了老街。老街尽头用一丛曼陀罗收尾,不知是刻意还是无心。我这才发现,左侧是逼仄斑驳的长墙,右侧是萋萋荒草,我与湘江的距离,就隔着一滩荒草。
渡船刚靠岸,船上下来几个人。我想都没想就跃上船,不顾后面的提醒:“别上去,船要开了!”船上的大姐笑道:“不要紧,船一下子不走。”也是,甲板上只剩她一人,得等人过河呢。她说,每逢淦田赶集,对岸龙船镇堂市村的人过河赶集,渡船拥挤,集市也热闹。
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,我曾在衡阳石鼓书院拍过蒸水和耒水汇入湘江,在巴溪洲拍过湘江上的飞鸟,在橘子洲头拍过落日黄昏,在铜官古镇拍过湘江北去。跃上淦田的渡船,我是想以更好的视角拍南来北往的湘江,拍琵琶状的琴洲,拍传说中的三国古城。
南来的秋水,正拐出漂亮的弧度奔向我,像特意拉近我与琴洲甚至古城的直线距离。我将手机对准远处,努力拉近镜头,仍只拍到影影绰绰的古城,还是古城基遗址上建起的仿古城楼。
波光潋滟的秋水,拽着我回到1800年前。
当是时,孙权与刘备正达成“湘水之盟”。刘备说,荆州的南阳郡被曹操占领,我们不妨以湘江划界,东岸的江夏、长沙、桂阳3郡归你,西岸的南郡、零陵、武陵3郡归我。为“防蜀湘南之渡”,孙权当即在长沙郡设建宁县,将靠近长沙的槠洲(株洲市东湖公园一带)设为县治。彼时江岸、河洲遍地槠树,槠洲之名因此而来。4年后,孙权趁关羽北伐曹操之际,派吕蒙偷袭南郡、武陵和零陵。3郡沦陷,“大意失荆州”的关羽被杀,湘沅流域的荆州6郡成了东吴的江山。
38年弹指一挥间。吴太平二年(257),15岁的少帝孙亮临朝亲政,将建宁县城迁至南边的淦田,新的建宁城南北长150米、东西宽100米。可新城才用9年,东吴又易二主,孙皓将县治迁回槠洲。
工业新城株洲已寻不到建宁古城的痕迹,只有淦田,残留一小段粘土夯成的古城墙。
我没见过具象的古城基,只能再次将目光锁定江水。当年的杜甫几次途经淦田,途经这一江水。
杜甫人生中的最后两年,在湘江上兜兜转转。大历四年(769),自长沙溯流而上的杜甫,准备投奔时任衡州刺史的挚友韦之晋。当他赶到衡州,韦刺史调任去了潭州。两艘船,可能就错过在黑暗的河流上。杜甫黯然调转船头,顺水回了长沙。老友重逢不过月余,韦之晋突然身故。颠沛流离又成为杜甫的日常,最后连生命也终结在漂泊的船上。
杜甫在湖南写下90多首诗。我在他写株洲的诗中寻觅,在高德地图上对应,寻到他宿过的凿石铺、花石戌,觅到他经过的渌口和空灵岸,找到他登过的挽洲,只是不见淦田——或许当时淦田没有驿站,杜甫未曾瞥见藏在荒草和藤蔓中的古城。
淦田,彼时或叫琴洲。清光绪年的《湘潭县志》里的淦田,是“淦田市(集市)”。因水运,一度“一巷三街六码头”,商贾云集,商铺多达80余家,每日停泊在港口的船只数以百计。而我在渡口,在江面上,只看到一两艘江轮。
从繁华9年的建宁古城,到明末清初的热闹集市;从淦田有了火车站,到站牌与火车站同时静默成京广线上的风景;从诸多码头剩一个渡口,到高速公路贯穿淦田……淦田,又在书写新的传奇。
古城往南5公里,现代化、智能化的淦田火电厂呼之欲出,2000吨级泊位的4个新码头蓄势待发,首台机组将于2025年年底并网发电。
古城往东3公里,“紫湖·归心谷”休闲农庄闪亮登场。邵阳商人老姚为妻子圆了“莳花弄草、修篱烹茶”的田园梦:梓湖水库边盖起的“归心谷”日趋完善,种在山岭的30万棵珍贵树木30年后会成林,7口鱼塘、3个荷花池供城里人休闲垂钓……老姚一家过上了归隐兼创业的幸福生活。
果实累累的柚子树环绕着大通间的木屋。书吧、茶吧、咖啡吧和烘焙作坊互不干扰,屋后是就地取材的红色砂砾岩墙。翻翻书架上的书,摸摸陶瓶里的干莲蓬,抿几口才煮好的黑茶,我的心彻底静了,在淦田老街和渡口的恍惚不再——我总算在新旧间找到平衡点。
想起老街,想起曼陀罗,想起渡口,想起那江水,想起古城遗迹,想起“归心谷”,想起大唐华银……我突然读懂了淦田。
- 新湘导读